
毕生过着书斋生活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却享有极高的公众知名度,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于“历史终结”的后冷战时代降临之际,无情地向美国和世界泼了两桶“冷水”——“文明冲突”以其惊世骇俗的论点令中国读者至今难以释怀,“我们是谁?”的警钟则长久地回响在美国社会的灵魂深处。亨廷顿曾因其观点的特立独行招致各路人马的口诛笔伐,然而在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即将开始之际回头来看,他的悲观预言似乎已经超越了抽象教条的学理和狭隘短视的政见,正在波云诡谲的世界形势中愈发清晰地变成现实。
不过,亨廷顿并非一贯的悲观主义。在他的主要学术作品中,至少有一部明显洋溢着乐观情绪,即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American Politics)。这本书的知名度虽然不及前述的两本“泼冷水”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谁是美国人》),却是了解亨廷顿本人的政治信念及其变化历程的关键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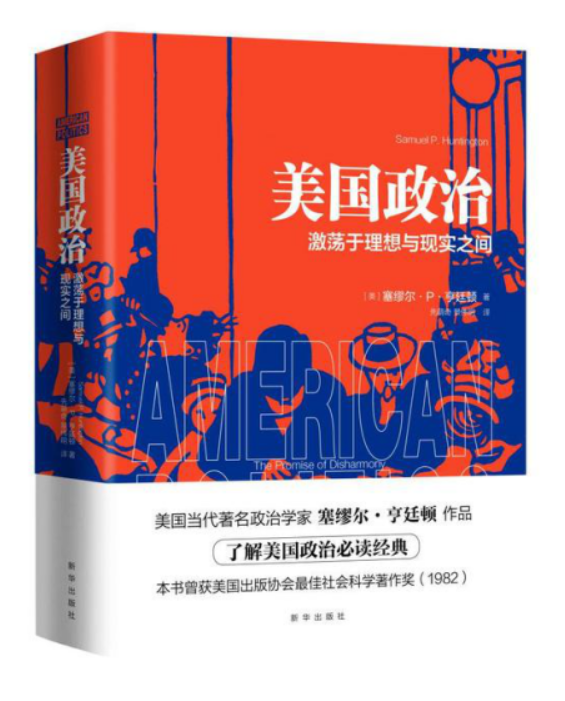
《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
ISBN:978-7-5166-3030-3
新华出版社
定价:59.00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经历了南北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内部危机。以战后婴儿潮一代为主力的抗议运动,围绕反战和民权两大主题,提出一系列激进改革诉求,并为此持久地开展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整个国家也随之陷入分裂与冲突之中。这段混乱的岁月就是亨廷顿写作《美国政治》的契机。他没有囿于就事论事的狭隘,而是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处,将这段历史归纳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周期性动荡。通过总结周期规律,分析其背后的动力原理,亨廷顿反而得出了一个积极的结论:隔几十年就要爆发一次的“激情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高度单一化、高度理想主义的产物,是美国自由主义革旧图新的自我涤荡。
所谓意识形态的单一化,指的是“美利坚信条”(American Creed)的绝对主导地位。美利坚信条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宪法的法治等一系列美国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集合,它跨越了几乎所有的阶级、种族、地域和职业界线,成为全体美国人的政治信仰和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而任何与之竞争的价值体系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美国人为之彼此争吵的,恰恰是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没有人会从根本上否定美利坚信条及其承诺,一切分歧终归只是实现自由主义理想过程中的时机、手段、速度和日程安排问题。
美利坚信条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导致其内部分歧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社会抗议与改革诉求。亨廷顿由此提出了“信条激情”(creedal passion)概念——拒绝接受不符合理想状态的政治现实,并对此提出激烈的道德批判和抗议。信条激情的爆发具有周期性特征,如果美国社会正处于对美利坚信条高度虔诚的信仰状态,并且清晰地感知到政治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信条激情就会喷薄而出,席卷政治生活的每个角落。除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战与民权浪潮,美国历史上还有三次信条激情的大爆发——18世纪中期的独立战争、19世纪20年代的杰克逊主义改革以及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正是由于信条激情的自我批判与修正作用,美国社会才保持了进步的发展方向。
《美国政治》从谋篇立意上就是要褒扬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理想。经过轰轰烈烈的六七十年代,作为国家认同根基的美利坚信条历久弥坚,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经受住了国内外环境的变迁与冲击,这是作者所乐见的。亨廷顿素以冷静的现实主义风格而著称,却在该书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意识形态胜利的乐观自信情绪,这在他的学术写作生涯中实属少见。
亨氏作品以高屋建瓴的视野、重章叠唱的文风和引经据典的论述见长,但也正因如此,读者常被笼络入貌似颠扑不破的阐述框架,在叹服作者深邃洞见的同时,忘记从中“跳出来”以独立审视其观点。事实上,单就《美国政治》而言,亨廷顿抓住自由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大书特书,却忽视了自由主义普世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张力。
亨廷顿显然是“美国例外论”的信奉者,却首先借助美国意识形态的普世性来论证其特殊性。他认为,其它民族国家通常借助前现代的非理性因素来提供内部凝聚力,而将合众国人民维系在一起的是依据理性原则得出的现代政治观念。“对大多数人而言,民族认同是长时期历史的产物,需要有共同的祖先、历史、种族背景、语言、文化,一般还要有共同的宗教。因此民族认同具有有机特征。然而美利坚民族却有所不同。美国民族主义是政治的,而不是有机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亨廷顿同样选择了“有机”路径,追溯至早期殖民地的清教传统,用一神论宗教的彼岸思想解释世俗政治意识形态的激情现象,并在实证层面上寻找社会宗教运动与政治改革浪潮之间存在周期性关联的证据。最初的英格兰清教定居者将北美殖民地视为宗教道德理想的终极寄托和建立至善社会的宏伟实验——“亚美利加大陆是为了纯洁的人性,它的存在是为了人类的进步与福祉。”随后在美英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清教徒的普世理想与近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其中蕴含的道德激情和理想主义也被美利坚信条所继承。因此美国是“一个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其政治生活就是以美利坚信条作为“彼岸承诺”的世俗宗教。宗教式的理想不仅意味着与现实之间永恒的差距,还意味着它不能被修改或放弃以迎合现实,美国维持其存在意义的根本方式,只能是为了更加接近理想的彼岸而不断地发动十字军式的道德斗争。
或许在亨廷顿看来,在特殊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反复“横跳”并未有损于逻辑的自洽性,毕竟美利坚信条只是继承了英格兰清教徒的道德理想主义传统。它是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认同,种族、宗教之类的“有机要素”已经被排除在外;来自天南海北、肤色信仰各不相同的移民,只要在政治上认同美利坚信条的价值观,就足以在文化上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站在80年代的门槛上回望刚刚结束的动荡年代,进步主义改革收获颇丰,保守主义思想适时回潮,对于兼具自由主义灵魂和保守主义头脑的亨氏来说,如此“金色池塘”般的和谐氛围可谓再合适不过。遗憾的是,亨廷顿难得的乐观情绪,终究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盲目的。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粉墨登场四年以来的种种光怪陆离——甚至更近一步,只看多灾多难、一言难尽的2020年——就足以让人怀疑美利坚信条神话的成色。
2008年,亨廷顿先生与世长辞。彼时的美国正在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尽管奥巴马高呼“变革”口号当选总统,预言中的信条激情火山却迟迟不见喷发。当然,美国社会并未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但其反应绝非共同价值观前提之下的“兄弟阋于墙”,而是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左右两翼的激进化呈现出相互刺激、螺旋升级的恶性循环趋势。从亨廷顿当年的论述来看,桑德斯和众议院“四人小队”代表的当今激进左翼,尚可以追溯至信条激情传统暗含的进步主义倾向;而鼓吹白人至上、排外主义和宗教保守的形形色色的“另类右翼”(Alt Right)运动,则完全与亨廷顿描述的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和普世国家认同背道而驰。
亨廷顿错了吗?很可能是的。事实上,他在冷战结束之际就开始意识到问题所在——过分低估“有机要素”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性。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就是亨廷顿在乐观情绪消散后重归现实的第一步。其实早在《美国政治》中,他已经为自己预留了修正观点的空间。他在末章分析美利坚信条的未来时写道:“作为有效运转的民族社会和政治实体,美国存在的时间已经超过两百年,未来的它也许不再那么需要以信条理想定义国家认同。数个世纪以来,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了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和共同经验,这些也可以用于定义美国认同,而抽象理想和价值的重要性也许会下降。国家认同的观念基础可能会被有机基础取代。‘美国例外论’将会消失。美国不再是“拥有教会灵魂的国家”,而会变为拥有民族灵魂的国家。”
号称普世价值的美利坚信条却能同时充当国民共同身份的基石,实际上是帝国与民族国家同构性的结果。上个世纪之交的美西战争既是美国向两洋进军的起点,也是美国第一次形成统一的国民精神。从此以后,美国现代国家的历史与其全球扩张的历史同步发生,主导并受益于全球化进程的自由霸权帝国部分掩盖了民族国家固有的排他属性,基于普世、开放、理性的帝国正当性不仅被用于“说服”他人,也被用于说服自己。然而,帝国也可能为自由开放体系所拖累,如果从中获得的边际收益越来越少,外部挑战者和内部空心化导致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朝着主权民族国家方向收缩和降维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意识形态的主流也会相应地从现代和开放回归传统与保守。
随着全球化反噬自由帝国的风险愈发显著,亨廷顿思想的转变已经远远不止于“修正”——2004年的《谁是美国人》几乎彻底否定了33年前的《美国政治》。现在他相信,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也需要用种族和宗教来划定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不但当下如此,未来应该如此,历史上更是一贯如此。美国自由主义仍然是国家认同的核心,但亨廷顿为其添上了“盎格鲁-新教”前提。他在《谁是美国人》中明确指出,作为纯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利坚信条已经不足以有效维持美国认同,美国“可以有自己一套信念,但其灵魂则是界定于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英雄与恶人以及胜败融入,这一切都是珍藏于‘神秘的记忆心弦’”。具有普世性的政治理念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凝聚为一个共同体,但是这些价值观恰恰是最初的清教定居者自身信念的投射,是独特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之人的产物。因此,维持白人新教徒的主流社会地位,才是关系到“美国之为美国”的头等大事。亨廷顿甚至在书中匿名引用《美国政治》的内容,将其作为错误定义美国认同的典型加以批判。种族血统和宗教信仰不仅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冷战后世界政治新的坐标系。在“文明冲突论”搭建的冷战后世界政治新范式中,美国不但要明确其盎格鲁-新教文化属性,还肩负着领导、保卫以基督教为核心纽带的西方文明共同体的责任。
是的,亨廷顿的确曾经错了,但他凭借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做出了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正确地预见了今天的美国与世界。至于未来是何光景,斯人已逝,我们已无从得知亨廷顿先生的看法。身为传统政客的拜登能让美国回归信条激情的进步周期吗?亦或是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继续流毒于天下?亨廷顿为《美国政治》英文原版拟定的副标题是“不协调的承诺”(a promise of disharmony),意指信条政治浓重的理想主义气质,注定使美国政治的实践永远无法完全兑现高高在上的彼岸承诺。未来的美国社会也许仍然会为征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而发动斗争,但在此之前人们可能需要首先争论清楚,美利坚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先萌奇)